布莱恩·普查曼的
《警察国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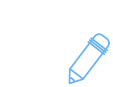
张建伟
美国学者布莱恩·查普曼(Brian Chapman)著有《警察国家》一书,此书中译本由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78年出版,朱坚章主译。该书追溯了西方世界警察国家的历史和成因,分析了警察国家的特征与趋势。在我有限的阅读范围内,还没有见到过第二本同一主题的书,此书弥足珍贵,是不消说的。
警察国家(police state)一词是上世纪三十年代末期由德文(palizestaat)翻译成英文。对于“警察国家”所下的定义是这样的:“该术语习惯上被用来不分意识形态地描述任何一种不受社会控制地使用有组织暴力的、强制性手段可以任意滥用或者有组织暴力和强制性手段只为统治上层目的服务的政治体制。这意味着没有法治,或者没有独立于警察和统治者的自治法律机制——“在这种国家里,警察对法律有广泛的、毋庸置疑的解释权。警察能够逮捕,长期监禁被捕者,使用刑讯,为其自己的目的解释现有法律,并推翻独立的司法调查结果。警察对于自己的预算拥有大量的自主权;他们甚至有权在从群众那里勒索钱财,进行犯罪活动,为自己筹措资金。其主要目标是镇压统治者和他们自己认为不合意的一切活动。”
毫无疑问,警察权具有保障人民安全、促进人民福利、改善社会等重要而积极的机能,为国家与社会不可缺少的公共机制。不过,警察权如其他国家权力一样,很容易被滥用。特别是,基于这种权力的性质,与其他国家权力相比,它更容易走向暴虐与专横。查普曼在书中分析说:首先,警察权天然具有武断的性质,“无论警察权如何在形式上受到适当程序、客观专家的证据或独立的裁定等主张的控制,它们的应用乃属于警察工作范围之内,而那基本上必然就是武断的。”此外,“无论理论上法律规定得如何紧密,在实际上法律之应用是随意的及不明确的。现代警察权力的部分性质便是有选择性的,而依定义说,此即意含选择权,在现代的社会里中,行政之复杂程度使得如果所有的法律及警察法令全部执行的话,所有的市民将会成为犯罪者。不仅如此,警察权具有武力性质,“警察的权力最终基于正当合理使用武力是无可置疑的。物理的强制力是国家的特质之一,因而在这方面警察武力(及军人)则是强制力的代理人(行为者)。” 权力都有滥用的倾向,警察权力也不例外,“警察使用武力超过其达到目的之所需,或是以不正当合理的手段运用其武力。”还有,“警察的工作在本质上是必须情报化的,因为这是情报的获取而不是罪恶的侦查,情报可使警察事先响起警报而提高警觉,而不是事后的补救。此项工作的大部分不免涉及到人民的自由,虽则他们没有意图涉入非法的行为,或没有明显颠覆意图的表示,警察只认为让时间证实谁是谁非,因此安全的代价是永久不断的警戒。” 总之,“警察权力的武断运用,残酷手段,侦查机密,企图使本身的命令称为法律等,都是所有警察系统的固有特征。这些特征源于警察工作的性质,很明显,现代科技的变迁已增加了滥用权力的可能性,手持警棒比之使用催泪弹是一种非常古老的手段,对于警察来说,则更具危险性;电力的使用比之电池的撞击远为有效;自从必须拆开信件的时期,通讯的截取已改变了它本身的性质。”
警察国家有传统与现代之分,查普曼解释说:“传统的警察国家在整个十八世纪与十九世纪初发展的时候所具有的一些基本特征,传统警察国家是由于改革与现代化的需求而产生,未来达到革新与现代化的目标,其创立者确定了一套结构化的社会模式和形式化的行政阶层组织,传统警察国家是基于社会和行政的合理分工而来,而其秩序,形式与纪律的官僚价值,则从官僚扩及公民的公私生活。” 在现代社会,英国人、美国人率先对警察人员及警察勤务抱持一种怀疑态度,对于“警察国家”一词也赋予其道德上的谴责的含义。尤其是纳粹德国兴起后,“警察国家”与德国建立的国家社会主义连接在一起从而成为负面概念,“警察国家”被定义为:“一个政治单元(如一个国家),其特征如下:由警察特别是秘密警察,运用专断权力,对政治、经济及社会生活作压制性的政府控制,而替代了政府中行政、司法机关所依据之已确立法定程序的一般运作。”这意味着它不是一个宪政国家,也不是一个法治国家,具有非理性、情感化与歇斯底里的倾向,违背了自由主义者的天性和具有善良意志的人类。
人们常将警察国家与纳粹德国联系在一起,“国家社会主义国家时代的德国,其行政历史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三九年,在此阶段中,德国的法学家以及后来的许多观察家,都认为德国具备了一个警察国家所有的许多特征,我们将视此时期的德国为现代警察国家(Modern Police State)。在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四年,产生了一种新的国家形式,极权警察国家(totalitarian Police State)。纳粹德国“经由宪法的变革,而使德国从自由民主政体转变为独裁政府。”另外,“实行永久紧急状态,以便日后在制度上或司法上的变革有合法的依据。”此时,纳粹党与国家合二为一,党的一些机构被赋予了国家的权力,“党有一个唯一的声音,此即领袖的声音。”于是“ 朕即国家”的现代版就出现了,“德国宪法中便产生了两个平行的法源:一则是国家权威,这是基于传统的宪法及行政与紧急状态,其乃提供维持政府的正常机能。另一则是法外权威,它是由领袖所赋予,完全以领袖的意志为意志,且其优于国家权威,因为随时单一指导的意志将公布其为权宜。因此,国家权威只不过是给予领袖的非正式的法令一个正式的印鉴而已。而党和警察则从法外权威中获得重大的利益。” 这一切都发生在纳粹党掌握政权之后,“国家社会主义政府于一九三三年取得执政权后,就开始组织了一个新的警察系统。”1933年4月26日颁行法律组织国家秘密警察,即“盖世太保”。法律的限制被打破,“在德国境内,地方允许警察之运作可不必顾及立法上对于其行动之限制”。希特勒“使警察成为他个人的工具”。在警察恐怖政策之下,司法组织受到影响,“此司法组织在欧洲国家中并非是最好的,许多优秀的司法人员均偏好探究司法学理的乐趣,而不喜欢担起法官的责任。在欧洲,司法是以其敏锐与富创造力的学理闻名,而司法之清明与自由主义却不出色。然而它毕竟是一个强大而有价值的组织,国家社会主义党持着与别国的激进分子相同的看法,怀疑司法组织太稳固、保守而缺乏改革的热诚。” 司法组织成为纳粹德国的新政策的牺牲品,“希特勒以帝国首相的地位获得了支配国家组织的权力;又以德国人民领袖的身份取得宪法外的权威。” 在这种情况下,“司法机关因此不得不适用残酷的法律。”由此一来,司法机关完全处于附属的地位。不仅如此,“在党与警察的控制下,设立了特别的‘人民法院’(People’s Court),负责处理各种的新犯罪案。警察执行及时惩罚(Summary punishments),传统的权力被大大加强了。同时,警察行政上引起批评的部分,追溯到往昔传统警察国家的事实,乃再次免于受司法组织的控制。就这样,不单只建立了一个与司法部门相平行的法律体系,同时也产生了一个司法行政上的平行体系;使得整个司法权力范围脱离正常司法的管辖,而落在由警察机构或其属下所支配的机关中。” 不仅如此,纳粹德国还“经由奇妙地使用文字、形式、与武力便使传统的司法体系化为无效。”
人们对于“警察国家”怀有恐惧心理,是因为担心“警察权力将会被蓄意地滥用,而警察机关及其人员将会以一种异常威吓的姿态出现”,在传统的警察国家里,“当时主要的恐惧表现在秘密的及不断的监视,这是十分为人所怨恨的”,经过极权警察国家的噩梦后,人们更希望有机构能够抑制警察的权力使之得到正当行使,司法机关对于侦查权的有效控制成为这一期望的寄托之所,“审判中心主义”在这种期待中应运而生。 人们通过完善刑事诉讼程序来规范警察行为,防止暴力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取证,全程录音录像,律师介入以及司法令状制度、司法审批等方式对警察权加以控制,防止“秘密的暴力”。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提出“公判中心主义”有抑制警察权的考虑。在日本战前,“日本的警察组织有一种像理念之监护者的地位——如果我们视强迫性的国家宗教与政治理念是同一东西的话。警察机关拟定警察规条法令取治理社会生活,注重‘思想控制’排除异己,因为它都认为是与内部颠覆的问题有关。警察局的神社部(Shrines)指挥国家神道的信徒(Shinto)本身是一种对天皇崇拜的制度表现,它透过行政管辖的系统可有效限制司法的独立。”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进行刑事诉讼制度改革,提出“公审中心主义”的改革主张,主要针对的是二战期间军国主义猖獗,日本的警察和检察官充当军国主义鹰犬的角色,“以侦查为中心”在政治意义上就是突出警察或者检察官的地位与作用,法官及其庭审工作成为检警的橡皮图章。 “以审判为中心”具有抑制“警察国家”形成的机制,可以藉此塑造法官、检察官、警察关系,提升法院的权威和法官凌驾警察与检察官之上的地位。
在现代法治社会,“警察国家”已经成为历史的一个梦魇,尽管如此,人们仍需要时刻警惕,并注重以司法权来抑制警察权,避免“警察国家”再度形成,正是现代司法制度与诉讼程序的使命。读布莱恩·查普曼(Brian Chapman)著有《警察国家》一书,看到他为“警察国家”勾勒的画像,可以对现代法治原则、司法制度与诉讼程序维护个人自由权利功能有一个新的认识,并获得“警察国家”的清晰概念,进而从历史与现实角度思考人类进步的意义。在我看来,这正是这一类书开卷有益之处。本文摘自第50辑《法学家茶座》



图片来自网络
欢迎关注我们

0
推荐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